
1
2014 年,我从父亲手里接下业务,成了天扬公司的一名供应商。天扬是本地开发区最大的企业之一,经营服装制造和销售。公司有 3 栋楼,一栋做行政用途,另两栋是制造工厂。
厂房第一层是底仓,从南门一直通到北门,推拉门一开一关,来料和出品都很方便。这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人来人往,领料的、对账的、从外面溜进来推销的,有时会排起长队。要是仓管员发错了材料,巴巴地喊车间来换,数目重新核对后,双方难免扯皮。若是流水线上出了纰漏,比如毛皮烫了、卷了,胶水使多了,线长就会来底仓,求仓管员 “施舍” 一点零头补上。
底仓的各个区域用草绿色的铁丝网隔断出来,职员们的工位一溜儿排开,琴姐坐在最里头。单从外表,很难看出她其实是一个普通职员 —— 底仓的女职员大多穿灰色工装,讲话风风火火,虎里虎气,一看就是厂妹;穿着稍微正式些的,手上的键盘从早敲到晚,一脸倦容,显然也不是领导 —— 只有坐在最里头的琴姐,穿西装套裙,化着淡妆,腰板挺得笔直,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又有一副从容姿态,一股子 “幕后金主” 的气质隐约透出来。
那时我初出茅庐,待人接物都很生涩,早听同行说天扬的老板娘姓沈,年纪不大却事必躬亲,时常在车间来回巡视,万一碰上了,一定得小心谨慎,要是被她抓住尾巴,生意就泡汤了。
第一次看到琴姐,我还暗自庆幸自己眼色利落,腆着脸凑上去,左一句 “老板娘”,右一句 “沈总”,叫得十分亲热。
她不怎么搭理我,我只好没话找话,一会儿问公司效益怎么样,一会儿又问她爱不爱吃海鲜:“我家亲戚跑了多年渔船,海货板正得很,我下回送点儿黄鱼过来。”
“我不是老板娘,只是个普通员工。” 她摇摇头。
我脑子一下没转过弯儿,不自觉地把这话当成了自谦,喊得更上头了。旁边的女会计看看我,似笑非笑,之后探过身子拍拍琴姐的肩膀,笑得很放肆:“你就别欺负他了!” 又转头对我说:“我刚来的时候,也把她当成老板娘哩。”
琴姐 “扑哧” 笑了:“我不是老板娘,你要是送野生大黄鱼过来,我倒不介意。”
原来,琴姐只是底仓的仓管员,负责清点、核对供应商送来的物料,签字确认什么的。闹了个大乌龙,我抓抓头发,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本地开发区的治安向来不错,天扬公司的老板只请了个老头看大门,一直平平安安。不料在 2016 年底,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天中午,底仓职员小叶在家和未婚夫吵了一架,到了上班的点,未婚夫一路尾随她到了公司。那男人喝了酒,闯进底仓撒酒疯,一脚踢翻了文件柜,把单据和资料弄得满地都是,又将小叶堵在角落里,两人厮打在一起。
保安亭里钢叉、钢盔什么装备都有,但门卫老头大白天睡觉,怎么叫都叫不醒。服装公司又以女性员工居多,底仓更是连一个男职员都没有,围观的女人们都慌了神,哆哆嗦嗦地不敢动弹。
这时,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琴姐挺身而出,她是东北人,个子却小小的,看上去一阵风都能把她吹倒。但她气场强大,先用锐利的眼神盯住男人,将小叶护在身后,从容地打电话报警。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终于惊动了行政楼的董事长,他带着一帮男员工涌进底仓,那男人才灰溜溜地离开。
事后,天扬公司换掉了看门的大爷,雇了两个年轻力壮的保安。
我问琴姐,当时为啥不害怕。琴姐就叹气说,没人出面,她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了。
2
几个月后,另一个供应商吴大姐很惋惜地告诉我们,小叶和未婚夫结婚了。本来未婚夫这样一闹,小叶决意分手,可娘家人却劝住了她。婚后,小叶让男人打得流产,精神也出了问题。听说终日躲在房间里,再也没有办法出门。
小叶是个很和善的姑娘。天扬公司有一位后勤杂工,是个哑巴,他衣着很寒酸,整天灰尘扑扑地搞废料清运,遇上人就 “呀哇呀哇” 地叫,谁见了他都躲着走。哑巴是计时工,干满一周就来底仓打单子,再去财务那里领工资。在底仓的一帮女职员里,只有小叶不嫌他脏,还怕他找不到出纳,有时会亲自领他去行政楼。哑巴也念她的好,特地从老家带土特产板鸭、腊肉、装在瓶瓶罐罐里的香油,一定要送到小叶手里。这是独一份,别人没有。
这么好的姑娘落得如此下场,与小叶共事多年的琴姐气得全身发抖,几乎掉下泪来:“我早说过,女人的心要狠一点,小叶太软弱了!狗改不了吃屎,那种撒酒泼的男人当断就断,绝对不能心软。”
琴姐吸吸鼻子,心情极坏:“女人一心软,就完蛋了。”
两年过去,我和琴姐已经混熟,就开玩笑说,琴姐肯定有故事。谁知琴姐顿时变了脸色,幽幽地看我一眼,没再说话。
一天下午,我去天扬公司办事,临走经过底仓,琴姐意外地叫住了我。她把我拉到一个堆放成品的仓储室,神秘兮兮地开口:“小弟,你是个好人,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她盯着我,迟疑了半晌,看起来很纠结,终于吞吞吐吐地问:“你跟行政楼的涂老师很熟吧?”
她说的涂老师是天扬的人事副总,原先当过中学教师。他平日里高高在上,极少下车间,底仓的职员很少有认得他的。我经常跑行政楼,倒是能跟他说上几句话。
“帮我问件事儿呗。” 她盯着我看,又伸直了脖子看向门外,确认周围没有第三对耳朵,“小弟,厂里要选‘管理’,我也想试试。”
“去呗,这是好事啊。” 我点点头,心底更加好奇了。
“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涂老师,咱们公司选‘管理’的时候,查不查背景呀?” 琴姐的声音依旧压得很低,看来这件事压在她心里很久了。
我问她什么是 “背景”,她说就是 “公安案底” 之类的东西。之前她在江苏上过班,那边的公司一般不限制基层员工的背景,不过在升职时是要做背景调查的。
我看看她,她也看着我,从她脸上微妙的表情里,我了解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查个鬼,就天扬?还查案底?” 我直摇头,笃定地说,“市区那边我不清楚,但开发区没有这种规矩的。”
本地治安不错,开发区的人员流动也不算频繁,换来换去都是那几拨,我从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要搞员工背景调查。听我这么说,琴姐似乎一下子就放松了,她点点头,轻轻说谢谢。
我悄悄地说:“琴姐,幸好你问的是我,没有找我爸。”
琴姐抿着嘴笑:“我可不敢找你爸,怕是要把我坑了。”
我哈哈大笑,琴姐看人倒是很准的。我爸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当面一套,背后又有一套。当年天扬有个外聘的欧经理,贵州人。老欧主政天扬时,我爸与他称兄道弟,可劲儿巴结。他父母从老家过来时,我爸先一步将二老接到宾馆,陪吃陪喝陪旅游,照顾得无微不至,大红包一个连着一个。后来老欧跳槽去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换了行业,失去了利益交换的机会,我爸就冷了脸。
现在,他还常把那套 “歪理” 灌输给我:“那帮外省的,指不定干过什么,谁知道好人坏人呢?有利益纠葛的时候,咱们巴结一下。要是失了势,那只好让他见鬼去了。”
3
没过多久,琴姐升职了。
这种事在开发区的企业里是很少见的。如今招工问题成了 “老大难”,不少企业更愿意将管理岗当作一种福利,奖励那些带人进厂的 “老乡头”。天扬公司里没几个东北人,琴姐一无文凭,二无人脉,居然奇迹般地晋升到了管理岗。
她的工牌换成了蓝底,比白底的仓管员高了一级,工资也翻了一番,还能进食堂的二楼小餐厅吃饭了。不过,她的工作地点仍然在底仓,外人难以想象她平日的工作量有多大。
我向涂老师打听,原来他这么安排,是存了另一层心思:琴姐能力出众,偌大的仓库让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如果陡然换个新人,多半撑不住。那就干脆给她加把担子,既管仓库又参与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升职也是笼络她。
一个公司里,下层职员是基石,那掌握实权的中层管理就是老板的 “触角”。逢年过节,供应商总要给他们送点小礼物,平日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为的就是多攒下几份人情,旺季抢订单会容易许多。县官不如 “现管”,琴姐的职位变了,我们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了。
第二年冬天,琴姐说她要回趟东北老家,拜托我开车送她。临上车时,她说先得去接一个叫小喜的朋友,那位朋友想送她。
小喜住一家东北饺子馆的楼上,在镇街的中心位置。她看着三十七八岁,个子高高的,扎个简单的马尾,很清爽,人一上车就打量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琴姐的同事。
小喜善谈,说自己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饺子馆,老公管后厨,属于 “技术入股”,年底有分红,他们夫妻尽心尽力,很勤勉。我说自己爱吃饺子,韭菜鸡蛋、猪肉大葱,什么口味都能接受。小喜很高兴,说南方人爱吃饺子的不多:“有空上我们店里吃饺子,给你包酸菜馅的。自家做的酸菜,和店里用的不一样。店里用的是市场买的成品,剁吧剁吧就完事,没有自个儿做的香。”
我们在前排胡侃,琴姐坐在后面一言不发。小喜告诉我,琴姐当年赚了很多钱,如今却连车都没有,语气很是惋惜。琴姐不乐意了,拍拍小喜的肩膀:“你扯些什么玩意儿,别乱说。”
小喜乖乖住嘴。回程路上,我问小喜,琴姐以前究竟是干什么的。小喜来了兴致,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
琴姐年轻时跟了一个社会大哥,他俩从小认识,算是青梅竹马。后来大哥开了一家公司,做的行当不怎么正派,因为放贷伤人、寻衅滋事,后来被判重罪,刑期两位数。
毕竟是自家生意,琴姐只能接过丈夫的担子,想把剩下的旧账和资金给圆回来。当然,期间触碰过法律的灰色地带,结果自己也进去了,在牢里蹲了 1 年多。刑满释放后,只有 30 岁的琴姐抛掉一切,决定南下讨生活。
“她爸妈都气出病了,养了好些年。琴姐一回去,他们老用话挤兑她,说得很难听,搞到后头琴姐两三年才回一趟,住两天就走。” 小喜说,“琴姐还不许我提。有啥好瞒的,重新做人就是了。”
“当过大姐头的人,怪不得,怪不得。” 我想起小叶那桩子事 —— 琴姐瘦瘦小小,光靠自身气势吓住了一个大男人,果然有两把刷子。
“她没干过什么坏事儿。” 小喜说。
我光顾开车,没往心里去,没有回应。
“你别不信,我姐她真不是坏人。” 小喜将沉默当成否定,特地转过头解释。
我点点头,说自己没有评价他人善恶的习惯,琴姐是我的朋友,这就足够了。
小喜不信,气呼呼地往后靠,车里的气氛闹得很僵。我有点坐立不安。一直将车开到饺子馆才松了口气。小喜下车,“啪” 地一下甩门,吓了我一大跳。
4
琴姐升职后,手里有了一点儿特权。她的工位旁边多了一圈铁丝网,面积扩充了不少,再挂上一把独立的小锁,忙里偷闲的时候,没人敢拿颜色瞧她。
小喜有时会来天扬坐一坐,带半份饺子,一些零嘴。她心大,时不时会用她那正宗碴子味儿的口音,透露一些消息。
她说琴姐之所以来南方,是想重新开始。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在南方找的,姓陆,苏北籍贯,两人认识了没几个月就闪婚了。婚后没多久,两人有了一个儿子,接着又有了一个女儿。
我十分好奇,问小喜,在浙江的东北人多吗?她说多倒是不多,但东北人自来熟,又爱唠嗑,很容易形成 “老乡效应”。从铁岭来的有一帮,“根据地” 是市区的某家浴场;从葫芦岛来的又有一帮,“根据地” 选在东北菜馆;她的同乡则集中在开发区附近的几家饺子馆里……
听我们吹牛,琴姐偶尔会插几句话:“中国很大,东北人在外的圈子却很小。” 她说普通话,据说是刻意练习过的,一点东北口音都没有。
仓库没有闲人的时候,她们会讨论一些比较隐私的话题,比如琴姐的文身。
琴姐身上的文身不多,显眼的只有两处。一处在脖颈后,一处在手背。前夫还没被判刑的时候,她文身是为了好玩,好看。等她后来在前夫的公司挑起大梁,手背上的那一排字母,则有了实际意义。
“上门讨债,看起来总要有点威慑力。” 琴姐少见地谈及过去的生活。
我脑海里浮现出古惑仔当街火并的情景,羡慕地说那一定很刺激:“在工厂上班多无聊呀。”
琴姐瞪了我一眼,说:“哪有那么威风?真正的马仔只有两三个,其他的全靠临时雇佣。钱到位了,人也到位了。要论生活,还是上班的日子安逸多了。”
琴姐说放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讨债也是门技术活。一怕债主自杀,那就摊上大事了;二怕公安上门,铁拳砸下来,多大的摊子都稀烂。那些所谓的 “黑社会大哥”,也只是在城市的犄角旮旯里讨食的人罢了。
总之,那两年做 “大姐头”,琴姐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现在,琴姐想洗掉那些文身:“那个王八蛋,胡扯什么中草药贴,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结果呢,是腐蚀性的草药,贴上之后痛得要命,跟酸洗没多大区别。”
她咬牙切齿地将脖子上的小红花指给我看,原先的图案已经模糊,只留下一团红色的烂肉,像是一块被烫伤的皮肤:“文身是洗掉了,这块皮也废了。”
她又将衣角挽起来,我才这知道她侧腰处有一朵精巧的花,像是梅花。表皮红红的,也留了一道丑陋的疤。她把衣角挽高了,露出了一大块雪白的腹部,片刻后,她似乎反应过来,“呀” 地捂住嘴,白了我一眼。我迅速移开目光,十分尴尬。
“身上的倒是无所谓,只有手腕那里没洗过了。这回必须小心点儿,可不能再信那些文身师的鬼话了。” 琴姐撇撇嘴,主动转开了话题,我接话说可以去医科大附院的皮肤科,水平要高得多。
“我听网上说,哪怕最好的激光洗,请最好的医生,还不一定能洗干净,总要留一点痕迹。” 她叹口气,露出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这种痕迹不是普通的伤口,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说如今文身已经成了风潮,年轻人在肩膀上纹一朵小花,手腕上弄两行字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琴姐摇摇头,说她洗文身是为了孩子。前段时间,她儿子转去了一所私立寄宿制的小学,她的压力顷刻放大了好几倍。这所私立学校去年高中部出了两个清华,小学部的学费跟着水涨船高,想进去的人挤破了头。为了让孩子读书,琴姐找天扬的老板娘帮忙,沈总也仗义,动用了自己的关系,前前后后颇费了一番工夫。
私立学校的家长们卧虎藏龙,条件都不错,周五去接孩子,校门口全是豪车。他们对孩子的要求也高,“家委会” 又是办读书会,又是办游学,还自发组织老师补课,翻印各种补习资料。
“奥数、作文、逻辑思维,有些课的名字我听都没听过。” 琴姐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琴姐的担心。她经济实力一般,儿子是外省籍的插班生,成绩也普通,要是让其他家长看见自己脖子上的小花,手腕上的字母,恐怕要炸开锅,说不准孩子都要被同学孤立。
“您想得太远了,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 我劝她放宽心,她皱起眉头,不说话了。
琴姐洗文身留下的疤,不仅在脖颈、侧腰,还在她的心里。
5
后来我才知道,琴姐早就对自己的后半生做了长远规划。
服装工厂分淡旺季,闲下来的时候,厂里只开基本工资,忙起来的时候,四脚朝天。时间就是订单,就是白花花的钞票,老板恨不得让流水线两班倒,上足 24 小时。偶尔遇到返工、剪毛之类的杂活,就要找外面的加工点帮忙。
除了上班,琴姐又到外头租了一间小房子,做加工之类的小活。她雇了两个熟练的老工人,将公司的单子派到自己手里,算是分一点汤喝。
有一回,她请我帮忙,将天扬的半成品送到那家小加工点去。我进了小出租屋,随意一瞥,就撞见了熟人 —— 那个叼着烟卷在机台上忙活的工人,不是天扬的张大头吗?
我和张大头是老相识了。他是个有名的烟鬼,一天要抽掉三四包 “雄狮”,熏出了一口墨似的牙。后来我听说他肺出了问题,回老家治病了。两年不见,怎么到这里了?
张大头见到我很紧张,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我心下了然,他大概是怕我会透风给天扬的管理层 —— 天扬是大厂,对员工派私活抓得很厉害,发现就辞退。
我说我是琴姐叫来帮忙的,他才松了口气。张大头说琴姐给了他一份不错的工资,比天扬高七八百块,他就过来了,已经一年有余。
“阿琴这个人呐,真拼命。6 点起床,她总要先来这里晃一圈,开了门,理一理货,接着回天扬上班。晚上 7、8 点,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又骑着小电驴跑回来,对一对数目,记上账。那丫头不用睡觉的啊?”
听着他的叙述,我心里颇有点不是滋味。琴姐平日衣着光鲜,很注重形象,干起活来竟比老工人还使劲儿。
事实上,为了留在南方生活,琴姐还有更拼的。
琴姐每半年要去献血一次,已经献 2 年了。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新居民的积分与公办学校的入学直接挂钩:“献一次血,新居民的积分能加 2 分呢。总共能献 5 次,我只剩下 1 次了。”
琴姐的儿子上了私立学校,但她经济实力有限,将来女儿能不能进这所学校是未知数。未雨绸缪总好过临时抱佛脚。
“儿子上私立,已经让他爸说了好多回了。但怎么也比镇上的小学强多了,那里的学生根本就不学习。” 琴姐想到了什么,语气里有一些很温柔的东西,“我儿子乖是蛮乖的,周末还会主动帮我洗碗、晾衣服,就是读书有点不上心。那小子啊,将来要是考个好大学,找个穿白衬衣的工作,不枉我花这么多钱。可别再像我一样混社会、混工厂了。”
这一瞬间,我对琴姐肃然起敬。我见过不少本地的新居民,对孩子的盼望就是多读几年书,不要当混混,将来进厂赚点钱好娶媳妇,就足够了。琴姐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奋斗,怎么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爬上去,她再清楚不过了。
6
上个月,我去天扬公司的财务部。天扬公司已经易主,管理层大换血,公司内部的形势变得相当诡谲。
我溜进了底仓,发现琴姐正在电脑前忙活,找她签单的、填表的、核对生产计划的,一个接着一个。她几乎没有休息的机会,只能偶尔端起茶杯喝口水。
琴姐看起来苍老了很多。难得她素面朝天,可以看到她浮肿的眼袋,皮肤也暗淡了不少。原本个子就不高,腰微微弯了一点点后,整个人就几乎缩水了 30%。
终于等到休息的空档,琴姐开始向我抱怨工作环境。前段时间,开发部弄错了工艺流程,厂长因此离职,新任老板却不肯再招人,似乎打算将这份细碎的工作分散到几个高管手里。
“资本家都是吸血鬼。” 我摇头叹息。
琴姐说,她恨死这份工作了。她干过仓管,又升职到生产部,可车间里一有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工人们都来找她,她几乎干了半个厂长的活儿。白天累得发慌,晚上却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脑子里都是入库单、返工单、工艺书、生产计划…… 即便如此,她还得干下去,天扬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天扬开出的薪水。
前不久,琴姐的丈夫买了个大车跑货运,外债借了四五十万,没跑几趟就出了大事故,万幸捡回一条命。事故之后的法律程序漫长而又繁琐,中间的弯弯道道让他俩筋疲力尽。
“有时候想一想,这日子过的还不如坐牢呢。” 琴姐咬了咬牙,将手里的记号笔远远地丢出去。她的手背上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看来前不久刚去洗过文身。
世事无常,琴姐的前夫如果不捞偏门,她也不会当上大姐头,更不会有之后的那些破事儿。如果没有那些磨难,她也不可能到南方来,从一个小小的仓管员做起,在第二场人生里忙忙碌碌,过一地鸡毛的生活。我不知该怎样劝她,只好闭口不言。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人间 theLivings 英文名:thelivings
-
免费下载或者VIP会员资源能否直接商用?本站所有资源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这里所提供资源均只能用于参考学习用,请勿直接商用。若由于商用引起版权纠纷,一切责任均由使用者承担。
-
提示下载完但解压或打开不了?1.最常见的情况是下载不完整:可对比下载完压缩包的与网盘上的容量,若小于网盘提示的容量则是这个原因。这是浏览器下载的bug,建议用百度网盘软件或迅雷下载。 2.解压失败:密码输入错误,请手动输入密码;不可在手机上解压,请务必使用pc端进行解压操作。 若排除上述情况,可在对应资源底部留言,或在“个人中心”中发起工单。
-
找不到素材资源介绍文章里的示例图片?对于会员专享、整站源码、程序插件、网站模板、网页模版等类型的素材,文章内用于介绍的图片通常并不包含在对应可供下载素材包内。这些相关商业图片需另外购买,且本站不负责(也没有办法)找到出处。 同样地一些字体文件也是这种情况,但部分素材会在素材包内有一份字体下载链接清单。
-
付款后无法显示下载地址或者无法查看内容?如果您已经成功付款但是网站没有弹出成功提示,请联系站长(doubaiwang@126.com)提供付款信息为您处理,或在“个人中心”中发起工单。
-
购买该资源后,可以退款吗?源码素材属于虚拟商品,具有可复制性,可传播性,一旦授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款、换货要求。请您在购买获取之前确认好是您所需要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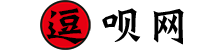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