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磕学君
我永远忘不了 1997 年。那一年,我 9 岁,长大成人。
那年夏天,一场洪水,夺去了我的父母。
白发人送黑发人,葬礼完了以后,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从记账人手里怔怔地接过仅剩的 10 块钱 —— 那是家里最后的现金了。
除此之外,还有几担子稻谷,一辆拖拉机,和一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着爸爸买拖拉机跟给我们凑学费借的钱,大概一万多的债务。
过了几天,债主纷纷过来对了借据,信用社管贷款的人过来把拖拉机开走抵债,家里就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了。
开学,学校不给减免学费,把当年新收的稻谷卖掉,只能勉强凑够一个人的学费。最后,把我留下来读书了,哥哥姐姐都借了别人的身份证出去打工,连车费都是借的。
有人说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我知道成绩比我好的姐姐放弃了学业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什么叫责任。
我的学业是哥哥姐姐放弃了自己最好的出路换来的,我至少得替他们争口气,我得把人生还给他们。
爷爷奶奶带着我们,用仅剩的那几担稻谷,度过了那个下半年。吃不饱,青菜吃完了剩下点汤底都舍不得倒掉,因为还有点油。
那段日子里,若要说吃过什么,我所能找到能吃的东西都吃过。
我知道生吃蕨根是酸的,但喉咙会很痒;
我知道新长出来的狗尾巴草的梗是甜的,只是吃得动的部分只有小指甲那么长一小段;
我吃过野生的芭蕉,虽然都是核,但是很耐饱,只是吃多了会拉肚子;
我吃过满身是刺的金樱子,虽然刺会扎伤嘴唇,但嚼着它,能嘴甜小半天;
我吃过从青到红的山捻子,那曾是我一年里最期待的美餐,因为它管够,漫山遍野,吃多少都没人管你,只是吃多了会便秘;
我吃过稻田里蹦跶的蚱蜢,抓一兜弄干净,摘点紫苏一起炒,很香;
我知道十月的田鼠最肥,鼠洞一头兜个蛇皮袋,在另一头用稻草点烟,浓浓的烟不一会就能把肥硕的田鼠赶出来;
我知道洪水中的鱼儿都昏了头,雨后洪峰过后,拿一个网兜,伸到浑浊的洪水里就能兜到一些小鱼小虾……
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当我把人生赚到的第一个一万块交给老人家时,两位老人眼圈发红,颤抖着手,数了一遍又一遍。
如今,我也一直在努力,希望得偿夙愿,把哥哥姐姐的人生还给他们。
来源:知乎日报
-
免费下载或者VIP会员资源能否直接商用?本站所有资源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这里所提供资源均只能用于参考学习用,请勿直接商用。若由于商用引起版权纠纷,一切责任均由使用者承担。
-
提示下载完但解压或打开不了?1.最常见的情况是下载不完整:可对比下载完压缩包的与网盘上的容量,若小于网盘提示的容量则是这个原因。这是浏览器下载的bug,建议用百度网盘软件或迅雷下载。 2.解压失败:密码输入错误,请手动输入密码;不可在手机上解压,请务必使用pc端进行解压操作。 若排除上述情况,可在对应资源底部留言,或在“个人中心”中发起工单。
-
找不到素材资源介绍文章里的示例图片?对于会员专享、整站源码、程序插件、网站模板、网页模版等类型的素材,文章内用于介绍的图片通常并不包含在对应可供下载素材包内。这些相关商业图片需另外购买,且本站不负责(也没有办法)找到出处。 同样地一些字体文件也是这种情况,但部分素材会在素材包内有一份字体下载链接清单。
-
付款后无法显示下载地址或者无法查看内容?如果您已经成功付款但是网站没有弹出成功提示,请联系站长(doubaiwang@126.com)提供付款信息为您处理,或在“个人中心”中发起工单。
-
购买该资源后,可以退款吗?源码素材属于虚拟商品,具有可复制性,可传播性,一旦授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款、换货要求。请您在购买获取之前确认好是您所需要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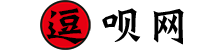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