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初三时,我家搬入新居 —— 那是彼时已经摇摇欲坠的国营厂留给很多像我家这样虔诚的职工家庭,最后的礼物。
房子是大人们说的 “公房”,厂职工家属楼,没有产权,已经住过不知道多少家人。它只有两间卧室,没有客厅,如果我能够原地腾空向上几米,应该就可以俯瞰看到墙壁呈一个 “日” 字,母亲要穿过我的房间,才能进入她的房间。屋里没有厕所,一层楼 4 户人,共享走廊的公共卫生间。
毕竟缺少一纸房本,房子严格意义上不完全归属自己,母亲决定不装修,直接拎包入住。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大件家具,母亲和继父分别从姥姥家和奶奶家简单收拾了几样刚需旧家具,请了一位拉三轮车的老师傅,来回跑了几趟,就归置齐全了。
搬家第一天,我发现家门口的墙壁上,有人用红砖写了一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后面还跟着一串加减题,字体歪歪扭扭。我猜应该是这套房子前一任住户家的孩子写上去的。我后来时常会在房子里探索其他人生活的痕迹,展开想象,推测前几任住在这里的房主们,他们家是不是都有孩子,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住在外面那间屋子。我很喜欢这句 “热烈欢迎”,讲不出原因,让母亲别擦掉它,母亲也没有当回事,她或许认为那间房是暂时过渡的一方住处,没认为那里是家。可我却和家门口那些稚嫩的字体一样,热烈地喜欢那里。我隐隐有种预感,我会在这间 “日” 字的职工家属房里,迎来我还不错的小日子。
那时我身体不太好,时常请病假在家休息。母亲怕我独自在家待着无聊,在逼仄的房间里为我腾出一小块区域,给我买了一台台式电脑,还专门购置了电脑桌。那一套装备耗费母亲好几千元,她或许压根没预感到自己即将下岗,不然一定舍不得如此大手笔。
崭新的粉色电脑桌和房间里年代感十足的家具风格很违和,电脑桌有专属的抽屉放置键盘,轻轻拉开抽屉,滑轨顺畅地将键盘送到我的面前。显示器有别于学校的 “大头机”,很轻薄。我打字速度很快,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出文字,一想到我是班级同学里第一个拥有电脑的人,我盲打的手指更加跳跃。
我房间有一扇窗户,推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架立交桥。每当有车轮飞驰碾过立交桥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和轮胎摩擦路面的噪音就合并撞入,到了寂静的夜晚,声响更是成倍放大。有一次,表妹到我家玩,夜晚留宿,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结果整夜翻来覆去无法入眠,说立交桥上传来的噪音吵得她头疼,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何能在震耳欲聋的噪音里睡觉。
事实是,那时我的睡眠质量很好,窗外的聒噪不过是闯入梦乡的一味佐料。噪音对我造不成困扰,要不是因为从立交桥吹过来的肉眼可见的灰尘浮扑进房间,我甚至不会将窗户关得严实。
2
母亲不喜欢这个房子,大概因为她住的地方前后对比过于强烈,带来了落差感。
上世纪 80 年代初,母亲高中毕业后进入国营保密军工厂上班,那时厂子效益进入鼎盛时期,职工的身份也水涨船高,本地人会毫不遮掩地向厂里职工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他们是相亲市场职业链条的顶端。
母亲长得漂亮,说媒的人频繁到访姥姥家。那时厂里的老职工们都希望子女嫁娶本厂职工,一来知根知底,二来 “强强联合”。母亲身边的大多女同学都嫁给本厂男职工,如今聚会时,她闺蜜们带来的 “家属”,也全是熟人 —— 大家要么曾经是班里的同学,要么是厂里的工友。这种情分沿着代际延续,我的发小们的父母,仔细盘点一番,也会发现他们都有交集。
可我母亲不走寻常路,她叛逆的结果是上了我父亲的贼船。
我父亲祖辈是地道老成都人,母亲初识他时,他的裤兜比脸干净,每天和狐朋狗友到处混,空有一张天花乱坠的嘴。我曾问过母亲喜欢他什么,她说:“你爸长得撑头(长得帅的意思)。”
母亲给父亲买西服,出资给他开了一家串串香店。她时常在厂里倒班后无缝连接去帮父亲守铺子,父亲则在家闷头大睡,太阳不落不起床。姥爷心疼母亲,拦着她,后来,串串香店关闭了,俩人又开了一家台球室。
结婚时,父母在成都的西门买了一套新房 —— 西门现在仍被称为成都的 “老富人区”。新房是三室一厅,大概有 120 平,母亲精心地为房子装修,安装了在当时十分新潮的吊顶,还在 80 年代末期斥巨资买了空调。
我出生后,父亲赶上经商好时代,生意越做越大,遍地开花,全国到处飞,经常不着家。我家衣柜里满满当当地装着母亲为他熨烫板正的西服,皮鞋油亮得可以照镜子。他每天把自己拾掇得光鲜亮丽,用摩丝把头发梳成大背头,每一缕头发,都彰显他的精致。
有天晚上,卧室的屋顶上爬来一只巨大的蜘蛛,母亲一晚上都盯着那只蜘蛛,完全不敢睡觉。她得随时挪动襁褓里的我,害怕蜘蛛失足掉到我的脸上。那以后,母亲对父亲频繁不着家颇有微词,可父亲举着大哥大牛 X 轰轰地告诉母亲,他出息了,母亲的好日子要来了。
只不过,母亲没等到他出息,只等来了他出轨。
父亲有计划地哄骗母亲,说打算卖了西门的房子置换一套更大的房产。等房子卖了,他卷走了房款,还顺手把母亲多年的存款也带走了。
3
我读小学时,国营厂迅速进入衰落期,正经历着多次改革苦苦挣扎。职工们没有上帝视角,预知不到危险的信号,大家安于现状,守着自己日复一日的工作,不温不火地每天重复 “四班倒”。
西门的房子被父亲卖掉以后,父母以离婚结束了拉扯,母亲的命运也随着国营厂一起,同步下滑。她手里再没能攒出多余的钱供她购置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便长期住在姥姥家。所以,搬入职工家属楼的 “公房”,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和母亲住在一起。
15 岁,我终于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了,虽然这间卧室还兼顾客厅的职能,可依然带给我梦想实现的快乐。我经常把发小喊到家里来玩,最夸张的一次,十来个好友挤在我小小的房间里,有 4 个人围在电脑前,还有 3 个小伙伴大剌剌地躺在我的床上睡着了。我和其余几个发小坐在地上打闹,期间推开窗向他们展示 —— 窗外的立交桥可真好看,就像一幅构图比例十分讲究的画。
有一天,我忽然听到楼下院子里有人在喊 “张潘生”,那个名字很难重名,我一下锁定那是我认识的张潘生。我站在窗前往楼下望,看到院子里发出呼喊的那个男生也是我小学同学。
张潘生的应答声从我楼上传了出来 —— 他居然和我是邻居,还住在我正楼上。
站在院子里的男同学也看到我了,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听到张潘生问他和谁在说话,男同学说了我的名字,我屏住呼吸想听楼上的答复,迟迟没听到回应。
张潘生是我小学同桌,是我在懵懂时期第一次产生湿哒哒情愫的人。他和我同是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袖子上挂着两道杠,小小年纪的我很欣赏他,认为他优秀又幽默。
一次课间时,张潘生提出要教我叠能浮在水面上的纸船,我咧着嘴答应。氛围极好,我头脑发热,一边折纸一边对他说:“给你说个秘密 —— 我喜欢你。”
张潘生倒吸一口气,一气呵成十分连贯地说:“我要(向老师)告你。”
我埋下头,余光撇见他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过得提心吊胆,很害怕凶神恶煞的班主任突然把我从教室拎出来,让我请家长。在我那时的认知里,“请家长” 这件事犹如灭顶的灾难,喜欢一个男生在灾难面前变得分文不值 —— 去它大爷的喜欢 —— 小小年纪的我,悲春伤秋地领会到一个真谛:爱情果然是经不起挑战的。
我们班在三年级时被解散了,张潘生和我分到不同班级,那些懵懂的情愫变成写尽的铅笔头,丢了可惜,拿在手里又太短了,握不住。不过,那场告白成为我高中时和闺蜜的一个谈资 —— 我可是小学一年级就敢表白的人,那时的我,可真勇敢啊。
我没想到,那场表白过去了 8 年后,张潘生竟然成了我新居楼上的邻居。平凡无趣的生活忽然被点燃了,引线呲呲地发出声响。我坐立不安,兴致勃勃地想问问张潘生,还记不记得那场幼稚的告白。
我有站在院子里那位男同学的 QQ 号,我赶紧打开电脑,在 QQ 列表里翻出他的头像,问:“你刚才在我家楼下喊的是张潘生吗???”
奈何,那时 QQ 尚未普及,他一个星期以后才回复我:“是啊,怎么了?”
我成功要到张潘生的 QQ 号。好友申请通过后,我战战兢兢地等待他的回复。张潘生说自从他知道我住楼下之后,也到处找人问我的联系方式。我嘴角都咧到耳根了。我俩都异常兴奋,对话框弹出的文字满满当当铺满了屏幕。
每次张潘生上楼时,他会把步子跺得很沉,我刚摸出手机,就看到他发短信告诉我,他从我家门口路过;职工家属楼房的隔音很差,他在家里弄出声响,我发短信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家里锻炼身体。
张潘生家里也有一台电脑,我们互相描述自家摆放电脑的位置,发现两家格局和电脑摆放方位完全一致,那感觉很奇妙,我把这一切归结为缘分。
4
我每天尽量在天黑前赶回家洗澡,每次都大包小包提很多东西,手忙脚乱地往走廊的厕所里搬。母亲把卷纸放厕所里,经常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只剩空纸筒,她也不计较是哪位邻居用了,毕竟邻里间都是熟人。直到我发现我的香皂被人用了 —— 这可无法忍受 —— 就彻底搬空了放在厕所里的装备。
赶上母亲倒晚班,我半夜想上厕所,那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挑战。我手握两把钥匙,一把开我家的门,一把开走廊厕所的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厕所冲。进厕所后,“嘭” 地一声关上门,迅速把门锁扣上,再蹲在厕所里平复心情。
厕所四面是红砖搭建的墙体,其中两面墙体嵌有红砖倾斜组合而成的镂空窗户,有次我把钥匙搁在镂空窗户上,扯浴巾时,钥匙滑到楼下,把一楼的雨棚砸出一个洞。夜晚的大货车碾压立交桥路面,会与楼体产生共振,我蹲在蹲便上,四面八方吹来的冷气就透过镂空窗户往厕所里卷,屁股被吹得凉飕飕的。
跟张潘生恢复联系后,我晚上去上厕所时,会提前给他发短信。他随后来到走廊上,用钥匙开他家走廊的厕所门,听到他的动静,我就不那么害怕了。很奇怪的是,我和张潘生每天无休止地通过 QQ 或短信聊天,却止于见面。我们住一栋楼,难免会在上、下楼的楼梯间碰到,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打招呼。
邻居都是国营厂的职工,张潘生的父母也不例外。他母亲很热情,经常拉着我母亲聊天,他母亲问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俩曾是小学同学时,张潘生总是找借口溜走,等他走后,我就说不太记得了。
2005 年,我升入高中,学校有别于我从幼儿园读到初中的厂职工家属子弟校,那里举目都是陌生人。在高一开学后的两个月,国营厂的土地开发权被一家知名地产商一举买下,职工家属楼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家家户户都在讨论一个话题:下岗。
我和张潘生都被家里保护得很好,那时我们压根不知道 “下岗” 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偶尔和张潘生聊起大人们的处境,我们两个的烦恼仅仅是怕随着厂子倒闭,“公房” 被收回,当邻居的缘分被剥夺了。
那之后没多久,窗外的立交桥开始变得出奇安静,一整夜,也没有一辆车驶过。国营厂里的老职工们,约好堵在立交桥口,闸断了出路,大家试图用螳臂挡车的方式,向羁绊和奉献了半生的厂子,讨要一个交代。
那一晚,整栋职工家属楼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其余的人都去立交桥入口静坐。我站在窗前,看着空荡荡的立交桥诡异地延伸到远处,桥两旁是星星点点的灯火,每一盏灯,都点亮一户人家。盯着这幅画面看得出神后,眼前的静态立交桥就变得陌生起来,孤零零地杵在那里。
这时,一只老鼠从窗前窜了出来 —— 那是我最恐惧的生物,因为它总在我不安无措时,跳出来威胁我。小时候父亲卖了西门的房子后,母亲只能租房子居住。那个出租屋周遭鱼龙混杂,隔壁住着一群瘾君子,警察曾破门而入抓捕他们。其中一个人为了逃避逮捕,当场跳楼,就躺在我家窗户下面。
那个出租屋铺着廉价的地胶垫,每天晚上都有老鼠在房间里窜来窜去,它们踩在地胶垫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吓得我整夜都不敢睡觉。后来,我去找父亲要生活费,他让我在他和小三买的新房里留宿,住在保姆间,那间房的衣柜里,也有老鼠。
老鼠强行中断我观察立交桥,我赶紧关上玻璃窗和纱窗,然后脚底一软,瘫坐在地面上 —— 老鼠把我拉回现实,我大口喘气,试图平复恐惧的心情。我在想,在立交桥入口坐着的那群人,和面前静态的立交桥相比,谁更孤独?
5
最终,国营厂以英雄迟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没逃过时代的碾压。
职工家属楼仿佛一夜之间罩上阴霾。大人们不再倒班后坐在小区里闲聊,他们的话题统一变成找工作。大家会共享招聘信息,下岗的女人们的出路大多是去超市里做促销员,男人们则去做门卫或者蹬人力三轮车。
那天,我照旧全副武装去走廊厕所里洗澡。洗完后,正准备收拾残局,一声闷响传来 —— 我的一串钥匙掉入厕所坑里了。上次钥匙掉下楼,母亲提醒我不要把钥匙放在镂空窗户,怕再次掉下去砸到路人。这次,我把钥匙放到水表上,却不小心掉入厕所坑里。
我没有带手机 —— 母亲下岗后不敢让自己闲着,家里连轴的重担压在她的身上,她面试了一份新工作,在公司加班加点冲销售业绩;继父每天晚上都有一场桌上四人砌墙运动,大部分时间,我都自己在家 —— 我裹着浴巾思考了很久,好像只能向张潘生求助了。
我第一次走上楼,通往张潘生家的楼梯间有一道防盗门,由他们那层楼的 4 户住户平摊费用购买安置。原本大家对于 “公房” 不愿多投入,认为它不是归宿,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点,但是,那段时间职工家属楼频繁遭到入室盗窃。
曾经有邻居打开自家大门时,一下从家里窜出 9 个毛头小伙子。我家也遭过贼,一天夜里,我听到有人在开门,以为是加班回来的母亲,嘟嘟囔囔说了一句:“回来啦?” 没有动静,我便继续沉沉地睡了过去。第二天起床上学时,我看到我家大门虚掩,门锁掉在地上,旁边散落一地的木头渣子。门锁周围,有很多小刀划痕。母亲吓坏了,赶紧把老旧的木头门换成铁皮门。
我在走廊防盗门处喊张潘生,他母亲听到了,了解我的窘况后,非常热情地带着丈夫和儿子向我伸来援助之手。
张叔叔撸开袖子,尝试伸手到厕坑深处捡钥匙,他毫不嫌弃肮脏的厕坑。邻居闻声而来,有人递来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尽头绑着一个金属钩子。张潘生操着一口四川话对我说:“莫来头,不虚哈。”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对我说的是四川话。
国营厂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建厂,建厂之初,响应国家支援三线战略号召的上千个工人,从东北浩浩荡荡地坐火车南下,到成都完成大西南建厂目标。大家背井离乡来到成都,从此落户于此,生活轨迹完全颠覆,世代都留在这里,为国营厂奉献一生。
国营厂有职工专属幼儿园、学校、医院、电影院,还有专属这里的 “厂话”。它的口音乍一听像普通话,仔细揣摩又渗透出些东北味儿,个别词语又蹦出四川话独有的语言习惯,夹杂着椒盐川普的味道。
因为父亲是本土成都人,我可以任意切换成都话和厂话。从小到大,我都在厂话笼罩的范围生活,厂职工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从国营厂里抽调而来,也都用厂话替代全民普通话。
张潘生的父母操着我熟悉的厂话帮我解决燃眉之急,可张潘生冷不丁地用四川话安抚我,让我有些别扭。我裹着浴巾,头发丝上的水珠滴滴答答地往地上砸,手臂冻起鸡皮疙瘩。我慌乱地抱着一堆瓶瓶罐罐,被热情的邻居们层层围住。
大家轮番尝试用竹竿去勾钥匙,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开始商量是否要暴力开锁,举着螺丝刀跃跃欲试。我站在那里,点头应和着,只想赶紧逃离大家焦灼的眼光。
那天之后,张潘生终于主动约我吃了一顿串串香。吃东西的时候,他接到他母亲的电话,明明手机那端传来的是熟悉的厂话,他却用四川话应答着。那一瞬间,我觉得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背叛了守候我们的一方土地。
那顿饭,我执拗地用厂话和他聊起我们的小学生活,那些缥缈的事情,实在太遥远了,好像都和张潘生的经历无关,他就像在听我讲别人的故事。
再之后,我和张潘生渐渐没有联系了。印象中张潘生最后一次和我联系,是我读高二时。当时他职高还未毕业,准备辍学去外地做生意。我们生疏地通过 QQ 告别,谁也没有越界。至今,我都没问过他,是否记得一年级时那场滑稽的告白,只是默默在内心与他达成和解了。
我有几个老同学和我一起升入同一所高中,那里是国营厂庇护范围之外的地盘,身边每个人都说四川话。我与那几位老同学单独相处时,大家也默契地说起成都话。
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逐渐侵蚀我们,大家为了融入新的小集体,在内心渐渐抛弃另一个旧集体。或许我那些扭捏的情绪,那些自认为坚守的东西,对张潘生而言,都太黏稠了。
6
高考后,我毫不犹豫地将 3 个志愿都填在本地。我从来没想过离开成都,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太美好了。
上大学时,我办理了住校手续,却时常走读,隔三差五就回家。我谈了一场恋爱,男朋友的方方面面都符合我对恋爱的憧憬,我早早判定他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那时我想时间过得快一点,我渴望自己早点满 22 岁,到达法定年龄,就可以和男朋友结婚。
每次我回家时,男朋友会陪我赶公交车,想把我送回家。每次,我都在下车后,把他打发走,不让他陪我走到家。
回家的那条路没有路灯,经常看到有酒鬼在树前撒尿。那条逼仄黑暗的必经之路,常年散发着尿骚味。彼时我再仔细端详那栋国营厂的职工家属楼,发现它已经被嵌入周边的高楼之中,被电梯房包裹,在这个夺目的城市里,显得太过贫瘠和单薄。
家属楼只有 4 层楼,外墙没有刷漆,红砖鳞次栉比地排列着。2008 年汶川大地震,房顶的红砖大块脱落,掉到院子里。后来,掉落的红砖被人堆在墙角,一直没人打扫,久而久之,成了堆垃圾的小土堆。
我家窗户前的立交桥,被政府围上隔音板,隔音板足够高,挡住了我的视线,推开窗户,再看不到川流不息的卡车。家门口红砖留下的 “热烈欢迎”,早已模糊不清了。
我在暑假时去过男朋友的老家。他家里的装修十分洋气,欧式风格,房子层高很高,客厅正中央吊着耀眼的水晶吊灯。男朋友的父亲为他购买了车库,计划等他毕业就给他买车。
在一个安静的深夜,男朋友怕我一个人回家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到楼下。我妥协了,我们手牵手走在那条黑暗的小巷子里 —— 那是我每次把电瓶车放进车棚后,需要自我鼓励打气、屏息快跑的一条小街。
路灯还没有点亮,路旁有几条流浪狗,墙上还蹲着一只猫。我一直以为猫和狗无法和谐地处在同一个空间,谁知他们互不打扰,慵懒地待在原地,界限分明。
周围都是职工家属楼,隔音不好,一个男人打喷嚏的声音在小巷子里格外清晰。我鼓起勇气向男朋友袒露我逃避他送我回家的原因,支支吾吾,才敢承认是心底的自卑作祟。我和他分享,说我的发小们都是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长大,大家经常互相串门,我曾因为搬进这里,特别开心,邀请 10 多个小伙伴来家里煮火锅庆祝,食材买了一堆,弄熟的没几个。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嫌弃那栋老旧的职工家属楼,我鄙视自己,憎恶自己,认为自己背叛了心里的那点情怀,对张潘生的疏离也让我羞愧。可是,我又很矛盾地渴望,我能拥有一套房子,房子里有属于我的卧室,还有卫生间。
男朋友揽过我,轻轻地给了我一个拥抱,用手拍我的后背。他个子很高,拥抱我时,我的耳朵刚好贴在他的胸膛。他说:“这都不是事儿。”
我分不清我听到的是他的心跳声,还是我的心跳声,总之,使人安心。
那之后每个周末,男朋友都会来我家吃饭。我去洗澡的时候,他会搬个凳子坐在走廊上玩手机。他帮我装着钥匙,等我洗完澡,他会帮我吹头发。
7
那几年,拆迁的消息从未间断过。2012 年,我大学毕业时,拆迁的靴子真正落地了。
邻居们可以无条件搬入另一所旧房子,产权从 “公房” 变为 “私房”,也可以添一笔钱,购买新房。综合拆迁优惠和职工的工龄优惠,添的钱不算多。
职工家属楼里的住户们陆续签了合同,相继搬走。每腾空一间房,就有人紧跟着上门,把门和窗户拆掉。
母亲选择购买新房,新房是期房,需要租房子过渡一段时间。租好房子准备收拾东西搬走时,我看到她眼里流露的不舍,拖拖拉拉了好几天,也没搬完,完全不像搬进来时那么利落。
我家这层楼的邻居搬走的那天,忽然来了一群陌生人,住进我家隔壁。窗户和门被拆掉了,我上厕所时一眼扫到屋里的情况,地面上横七竖八躺了好几个人,看穿着,是少数民族的打扮。他们在屋里架起柴火,柴火上炖着一口水壶。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我眼光和他们碰到一起时,吓得我背脊发凉。
我如临大敌,赶紧跑回家反锁门,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回来后,在屋里一番倒腾,收拾了好多旧衣服和棉絮被子,让我帮她一起抱到隔壁去。
我感到费解 —— 隔壁那群陌生人长得太凶悍了,我催促着母亲赶紧搬家。母亲却对我说,她看到住在隔壁的那群人里有一位孕妇,她还牵着一个小孩子:“门和窗户都关不了,他们太冷了,好心疼。”
母亲和那群人有方言障碍,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和他们沟通的,我站在门口,只看到房里的男人和女人们一个劲儿地给母亲鞠躬。回家后,母亲又让我把走廊上锁厕所的钥匙递给那位孕妈妈。我这次才敢直视那群人,那群男人身材高大,却腼腆地对着我笑,频频向我点头。
几天后,我们收拾完毕,正式搬离那栋职工家属楼。临走前,母亲和男朋友合力把家里的床垫搬到隔壁。
整个职工家属楼搬空了,转眼间夷为平地。几年后,一栋电梯房在原址拔地而起。
张潘生家也选择购置新房,他父母购买的新房和我们的新家一街相隔。如今,两位母亲买菜碰到时还会聊上几句。只是,没有人知道我家隔壁那些人的去向。
8
搬离职工家属楼不久,我和男朋友结婚了。公公为我们支付了首付款,购置了婚房。
还贷的第 7 年,我和丈夫攒够了钱,一次性结清了婚房的贷款。紧接着,于 2020 年 1 月,我们购买了第二套改善型住房。
在选购新房时,我俩曾光顾过职工家属楼原址建起的新楼盘售楼部。那房子是跃层,足够高挑、明亮,但是我们顾虑它临近立交桥,灰尘和噪音太大,最终没有选择那里。
最终,我们相中了一套 160 平的二手房,老房东是一对老夫妇,我们面对面坐在房产中介的签约室,价格谈好了,签约完毕,老先生缓慢细致地用了 1 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们介绍那套房子。
老两口不喜吵闹,极少邀请外人来家里做客。有位住家保姆照顾他们日常生活和房内卫生,每个月还会请保洁来大扫除。
其实他们不用介绍,我也看得到两位老人家藏在房子里的精致生活。阳台的一方地面,被用榻榻米垫高,上面架着一台钢琴,那是老奶奶陶冶情操的爱好,后来他们的孙女在玩闹时摔倒,头皮在台阶处磕破了,老先生就用泡沫条把台阶锋利处包裹严实。餐厅做了观赏性质的壁炉装饰,实木地板款式不新潮,却锃亮,镂空的金属花雕楼梯缠绕延伸。
相比对房屋的精心保养,老先生对房子充沛的情感更能打动我。他缓慢地回忆他儿子当年在这间房里备战高考,如愿考入航天航空类专业院校,毕业后去到川航工作。我的宝宝从小特别热爱飞机,听到这里,他用稚嫩的声音向老先生复述了《中国机长》里那个川航 3U8633 的故事。
虽然老先生极力建议我们保留房屋原本的装修,说他当初在每一处细节都选用最好的材质。但丈夫最终决定,敲成清水房,按我们喜欢的方式重新装修。他喜欢倒腾家里的装备,从装修到添置家具、家电都不用我操心。自动洗碗机、烘干机、扫地机器人,一切能节省人力的装备他都毫不犹豫地添置。我也不用带钥匙了,因为大门用指纹解锁。
一切都有尘埃落定的踏实感。
新房是四居室,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卫生间在我的房间里。新房的马桶有自动加热圈,有实时清风系统,卫生间不会有异味,温水冲洗功能对女生很友好。我对丈夫感慨,我再不用在深更半夜被迫穿戴整齐,如惊弓之鸟般奔出门上厕所了,也再没有人会猛地拉卫生间的门然后敲门催促我。
我可以安静地待在卫生间,有时玩手机,有时候发呆,在慢下来的时间里,时常梦回职工家属楼。成年人需要稳重、体面,那个毛躁勇敢的我,只有在货车车轮压过立交桥路面时,蹲在厕所里,和职工家属楼的楼体会产生共振。
母亲退休了,她和国营厂的羁绊经过筛选沉淀后,唯留下工友间的情谊。
她和那群工友经常相约去旅游,时常和我提起,说和她一起去旅游的哪个阿姨,曾是一起住在职工家属楼里的邻居,哪一层楼,哪一户,曾经和我有什么交集,如数家珍。
我脸盲,只知道那是一群在母亲朋友圈里举着丝巾、在风中摇曳、如花般美丽的女人们。
或许,“公房” 这个特定年代和体制下产生的事物,最终会在社会上消失。不过,它不是我人生的短暂过渡,它是养育我的一方故土。
我是那间房子最后的主人。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人间 theLivings 英文名:thelivings
-
免费下载或者VIP会员资源能否直接商用?本站所有资源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这里所提供资源均只能用于参考学习用,请勿直接商用。若由于商用引起版权纠纷,一切责任均由使用者承担。
-
提示下载完但解压或打开不了?1.最常见的情况是下载不完整:可对比下载完压缩包的与网盘上的容量,若小于网盘提示的容量则是这个原因。这是浏览器下载的bug,建议用百度网盘软件或迅雷下载。 2.解压失败:密码输入错误,请手动输入密码;不可在手机上解压,请务必使用pc端进行解压操作。 若排除上述情况,可在对应资源底部留言,或在“个人中心”中发起工单。
-
找不到素材资源介绍文章里的示例图片?对于会员专享、整站源码、程序插件、网站模板、网页模版等类型的素材,文章内用于介绍的图片通常并不包含在对应可供下载素材包内。这些相关商业图片需另外购买,且本站不负责(也没有办法)找到出处。 同样地一些字体文件也是这种情况,但部分素材会在素材包内有一份字体下载链接清单。
-
付款后无法显示下载地址或者无法查看内容?如果您已经成功付款但是网站没有弹出成功提示,请联系站长(doubaiwang@126.com)提供付款信息为您处理,或在“个人中心”中发起工单。
-
购买该资源后,可以退款吗?源码素材属于虚拟商品,具有可复制性,可传播性,一旦授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款、换货要求。请您在购买获取之前确认好是您所需要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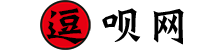
评论(0)